从弥尔顿关于出版自由的演讲到现代社会,追求新闻自由的斗争从未停止过。直到今天,新闻自由仍是一个复杂的话题。
《论出版自由》是英国诗人、哲学家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 1608-1674)于1644年向英国国会提出的一篇演说词,也是一篇争取出版自由的战斗檄文。
在这篇演讲中,弥尔顿充分发挥了其诗人的才情,以满腔热情控诉了规定“凡书籍、小册子或论文必须经主管机关或至少经主管者一人批准,否则不得印行”这一法令的《出版管制法》。他的演讲主要阐述了以下三个观点:其一,出版自由是人民与生俱来的权利;其二,限制言论自由就是摧残真理;其三,即经典的“思想自由市场”理论。
在演讲伊始,弥尔顿旗帜鲜明地指出了他要说明的三个问题。第一,“这法令(指《出版管制法》)的订立者是诸位不屑于承认的”;第二,“不论哪类书籍,我们对阅读问题一般应持有的看法。同时也要说明,这法令虽然主要想禁止诽谤性和煽动性的书籍,但达不到目的”;第三,“它(指该法令)的主要作用只是破坏学术,窒息真理”。下面,我将依照作者的行文逻辑逐一阐释上文所说的三个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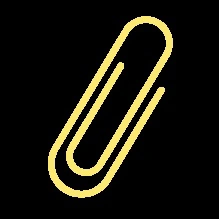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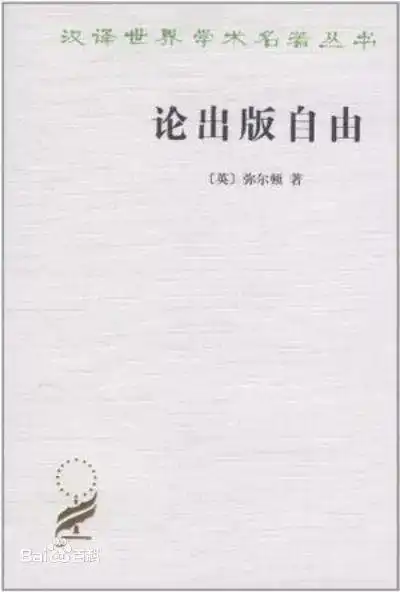
一、限制出版自由非法度清明之国所为
弥尔顿从一开始就竭力证明“古代一切法度清明、珍视书籍的国家都不会采用限制出版自由的许可制的做法”。西方人言古,必尊希腊罗马。弥尔顿引经据典,说明希腊罗马人对出版自由的充分尊重。关于希腊,他以雅典为例,“我发现雅典的长官只注意两种文字,一种是渎神和无神论的文字,另一种是诽谤中伤的文字”,而且管理方式多为事后惩戒而非事前限制。而在罗马,“早期宗教会议和主教们只是常宣称某些书不值得推荐或流传,读与不读却由各人的良心决定”。
显而易见地,限制出版自由的许可制之流并不是古代辉煌文明的遗产,而是从“最反基督的宗教会议和最专横的宗教法庭上发出的”。这一制度,有悖先贤所望。同时,这也说明,在古代先贤看来,出版自由是人民与生俱来的权利,而这一观点,应得到现代人们的认同。
二、阅读之利弊不在书,而在人
在第二部分,弥尔顿旁征博引,剑指许可制一直赖以存在的理由——“‘坏’的书籍腐化人”。从代奥尼苏·亚历山大,到《帖撒罗尼迦书》,到弥尔顿,他们均不认同这一观点。事实上,决定阅读到底是带来利或弊的,并不在于书,而在于人。“只要心灵纯洁,知识是不可能使人腐化的,书籍当然也不可能使人腐化”。这便驳斥许可制一直赖以存在的理由,即使是所谓“坏”的书,在心灵纯正之人看过后,并不会有“腐化”的结果,而是另外一种收获。
这种理念直至今日仍被许许多多的人认同。阅读之利弊不在于书,而在于人。阅读给一个人带来的是利是弊,取决于这个人如何,而非这本书如何。心灵之人,看到的是灵;心钝之人,获得的只能是腐朽了。限制言论自由,则是限制了人们听到不同声音的权利;而人们正是在不同声音的争辩、博弈中找寻真理;那么,限制言论自由,也就是摧残真理。
三、许可制是对学术和学者的巨大侮辱
在这第三部分,弥尔顿从希腊罗马转入当时的社会,满含愤恨地控诉了出版审查制度对知识分子的伤害。
在许可制下,书报检查员首先必须具备超越常人的学识与智慧,而这样富于精神和天才的人,又为何要从事如此枯燥无聊的书报检查工作呢?但是假如书报检查员学识不及作者甚至不及常人,让这样的人在自己的作品标题页后签署,这种做法,“对作者、对书籍、对学术的庄严与特权,都是一个莫大的侮辱”。
由此可见,无论从哪一面来说,书报检查、出版审查制度都是对知识分子的伤害,同时也伤害着执政者的威信和阅读者即人民的知识水平,是必须被取缔的。遗憾的是,这样的书报检查制度到今天,仍在不小范围内存在着。

四、“思想自由市场”理论
在演讲中,弥尔顿提出了著名的“思想自由市场”理论。他主张,“让一切思想都公开地表达出来,真理必定会在思想的自由市场上击败谬误”。
在这里,他给出了一个“市场”的概念。这个市场是一个平台,各种不同的观点、意见和思想在这个平台上公开辩论、自由竞争,最终产生真理。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弥尔顿的观点全部建立在一个基础上——他认定真理一定能够通过自我修正战胜谬误。我认为,这一点值得商榷,弥尔顿本人也并没有给出严密的论证。真理一定会战胜谬误吗?在不同观点的博弈中,最后胜出的就一定是真理吗?这些问题,都是不确定的。可以说,弥尔顿的这一认定,或许是有些“天真”。
但值得注意的是,1859年,约翰·密尔出版《论自由》一书,进一步发展了思想自由市场理论。密尔认为“迫使一个意见不能发表是一种‘特殊罪恶’”,因为“假如那意见是对的,那么他们是剥夺了以错误换真理的机会;假如那意见是错的,那么他们是失掉了一个差不多同样大的利益,那就是从真理与错误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对于真理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动的印象。”密尔发展了“思想自由市场”理论。从被发表的意见的正与误的两面展开分析,证明不管该意见正确与否,支持不同意见的发表有利于真理的产生,其逻辑更为严密,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弥尔顿的观点的“天真”。
五、现代社会的新闻出版自由和表达自由
从弥尔顿的演讲到现代社会,追求新闻自由的斗争从未停止过。直到今天,新闻自由仍是一个复杂的话题。读罢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对比现代社会的新闻自由现状,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思考,有待讨论。
首先,关于概念的界定。表达自由是指“公民在法律规定或者认可的情况下,使用各种媒介或者方式表明、显示或公开传递思想、意见、观点、主张、情感或信息、知识等内容而不受他人干涉、约束或者惩罚的自主性状态”。而出版自由则是表达自由的下位概念,二者是种属关系。事实上,我们不难证明,有出版自由,才会有真正的表达自由。如果个人的意见观点不能得到出版或发表,即无“表达”的机会,又何来表达自由一说呢?
其次,在现代社会,关于新闻自由的一个明显问题即为“记者证”、“许可证”问题,甚至因此衍生出了“假记者”之说。然而,仔细分析之下,“记者证”制度是严重妨碍新闻出版自由的,“假记者”之说更是站不住脚的。既然表达自由和出版自由的主体是“公民”,那么又何来“记者证”一说呢?只要在合法范围之内,人人都可以报道、传播,人人都是“记者”。
然而,虽说“假记者”是不存在的,但以记者身份进行敲诈的现象却存在。若要说来,这一现象倒是十分有趣的。这里我举山西矿难报道中“真假记者”为例。
2008年10月27日,中国青年报独家首发了山西霍宝干河煤矿矿难记者领“封口费”事件第一篇报道。该系列报道共刊登了18篇报道,其中《真假记者排队领“封口费”》、《端着新闻饭碗的丐帮》、《新闻出版总署通报“封口费”事件处理结果》为代表作。在山西的矿难中,矿方为了向上级隐瞒实情,为各路拿着照片而来的“假记者”发放封口费。
这些“记者”以照片为筹码进行勒索,但在这一勒索行为中这些人的定位又值得商榷。假如他们勒索成功,照片没有被发布,那他们不是记者,是彻头彻尾的骗子;但如果他们勒索不成功,照片被公之于众,那他们反倒成了真正的记者,尽管这与他们的初衷不符。这一现象在山西屡见不鲜,甚至形成了相关的产业链。在“真假记者”之间,出版自由的要义值得仔细思考与讨论。
最后,我想谈一谈在新媒体坏境下的新闻自由。在新媒体时代,网络空间给了使用者表达、获取信息的广阔平台,公民可以通过新媒体制作并传播新闻,公民的新闻自由权需要得到法律的保障。由此,表达和出版自由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保障。
阅读书单:
涂尔干《自杀论》
吴飞《自杀作为中国问题》
密尔《论自由》
弥尔顿《论出版自由》
徐艳蕊《媒介与性别》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