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又是靖江?


划开手机,热搜上那几个带着小城名的词条一蹦一跳,熟悉得让人想哭。

很多人压根没把靖江当回事,地图一缩,它也就是长江拐弯处一小块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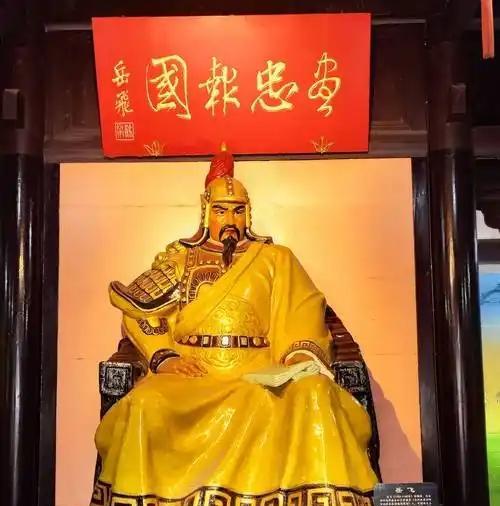
可真待过的人知道,那种“没人注意”的错觉有多害人。

先放个冷数据。

全市120多万人口,超过三成干的是配套制造业:精冲、液压、船配、汽配。

一家小厂只给高铁做弹条,一年产量能绕地球两圈半;另一家十几口人的工作室,专啃“风电法兰”,全球前五大整机商全用他们家的货。
听上去像吹牛,可出口报关单上确实盖着“靖江”章子。
外地朋友常问:既然这么牛,怎么连高铁站都还没通?
真相扎心:通高铁得先“让”桥,江阴大桥已经够忙了,再架一条就得跟上海抢航道。
靖江人等了二十年,最后等来句“先缓一缓”。
于是全市人民一起把私家车跑成了“移动大巴”,苏南的订单、苏北的人工,早晚高峰在夹江码头上演“水上堵”。
别看交通拖后腿,房价一点没落下。
老城区一条人民路,拐三个弯的学区房去年冲三万。
小年轻算了笔账:在靖江拿一万月薪,房贷八千,日子紧紧巴巴。
想跑?
上海、苏州都伸橄榄枝,“挖人”电话打到丈母娘手机上。
可往往上午还在外滩喝咖啡,晚上就回靖江吃馄饨,“通勤两小时”从段子变成了活地图。
靖江的尴尬,也是县城青年的共同困境:出去,舍不得家里味道;留下,又被房价追得上气不接下气。
有人硬是把困境玩成了花。92年的陈宇,大学毕业回家,把母亲做了一辈子的小吃“猪肉脯”挂上网。
第一年月销三百包,第三年双十一爆了八万单。
问秘诀,他抖抖肩:就是把小时候吃的那口甜咸记忆拍成短视频,网友闻着味就冲过来了。
如今厂子雇了五十个阿姨,切肉、腌料、翻锅的动作像提前录好的广场舞,整齐又治愈。
不是每个故事都一帆风顺。
城南的赵叔,60岁,做船板焊接到退休。
疫情那几年外贸单突然蒸发,他蹲码头刷手机,看年轻人点外卖比自己焊钢板还熟练,心里发慌。
市里搞夜校,他第一个报名,现在举着焊枪直播,账号名就叫“焊武帝”,粉丝天天蹲他讲焊缝里的“人生哲理”。
城里最大的广场夜里十点还亮着灯,一群宝妈推着车练地摊英语。
摊位摆的是外贸尾单童装,嘴上念的却是“free shipping”。
她们说,等哪天江阴二通道开工,靖江真通高铁了,这些句子也许能派上用场。
靖江像一块刚出炉的蟹黄汤包,鼓囊囊的,一戳就滋汤。
表面平静,里面烫嘴。
没有大城市的霓虹滤镜,也没有乡村的自在空旷,好处坏处都摆在台面上:
——想安稳,你得先接受慢;
——想冲一把,你又能摸到世界的边。
最后一班车轮渡的汽笛响起,有人赶着回江北的宿舍,有人抱着电脑留在江南的咖啡厅。
同一座小城,两条路,怎么走都有人声吵吵闹闹,提醒彼此:别装睡,梦还得自己做。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