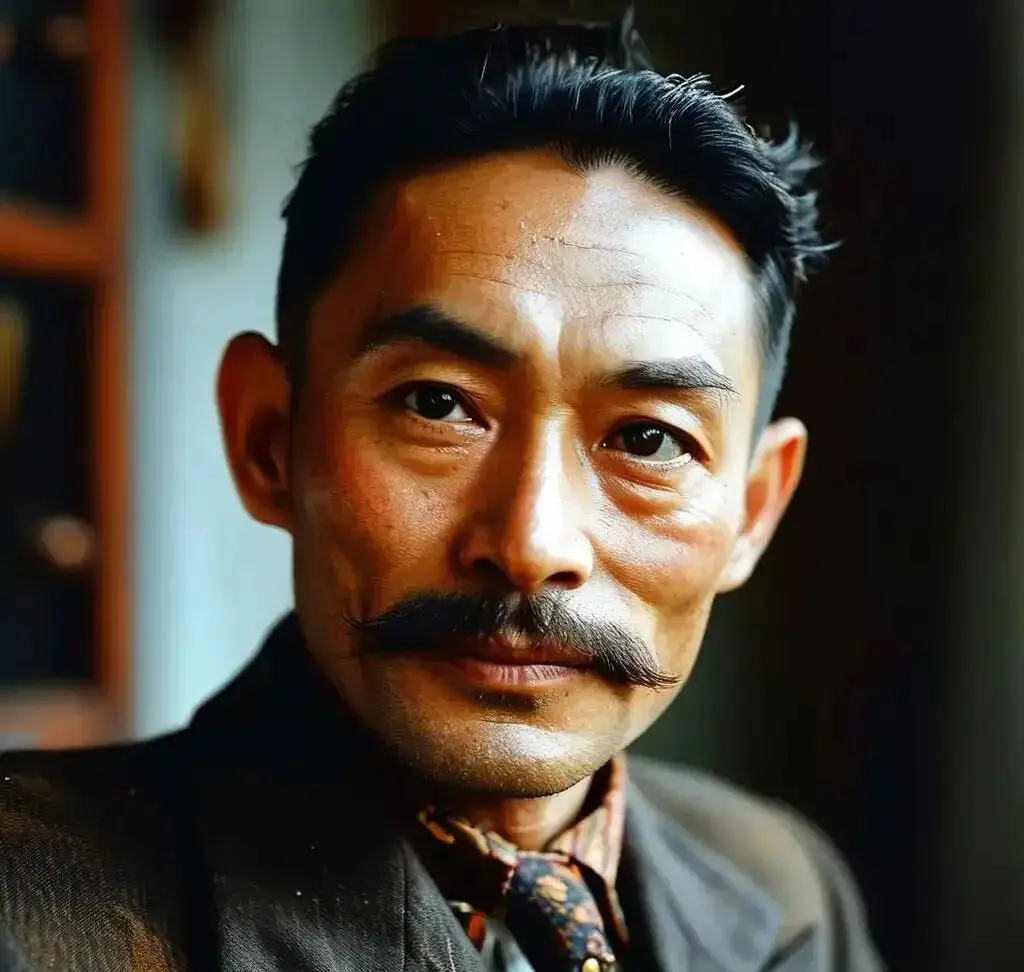
第二章
百斧劈开上海滩
三个月后的深夜,上海老城区的铁匠铺还亮着灯。火星子从炉口蹦出来,落在王亚樵的粗布褂子上,他浑然不觉,正盯着铁匠把烧红的铁坯锻打成斧形。
“王先生,一百二十把斧头,都打好了。”铁匠擦着汗,指着墙角堆得整整齐齐的斧头。斧刃闪着寒光,木柄上缠着粗麻绳,握起来格外扎实。
王亚樵拿起一把斧头,掂了掂分量,斧刃在油灯下映出他的脸。这些天,安徽籍的劳工接连来哭诉:洋行老板拖欠工资,青帮门徒强抢货物,报警没用,官府根本不管。“他们怕枪,怕权,可他们怕不怕拼命?”他对着工人们说这话时,眼神里燃着火。
第二天清晨,洋行的铁门刚打开,王亚樵就带着一百二十个劳工站在了门口。每人手里一把斧头,斧刃朝地,却透着逼人的气势。老板从里面探出头,看到这阵仗,顿时脸色发白:“你、你们想干什么?”
“给工人发工资。”王亚樵往前走了一步,斧头在手里转了个圈,“昨天你让青帮的人打了要账的老李,今天要么把欠的钱都给了,要么我们就拆了你的洋行。”
老板慌忙喊人:“快!叫巡捕来!”可话音刚落,就见几个黄包车夫跑过来,低声道:“王先生,巡捕房说没空管这事。”——整个上海滩的黄包车夫,早成了王亚樵的眼线,哪里有动静,他第一时间就能知道。
老板还想耍赖,王亚樵突然举起斧头,朝着旁边的木柱劈下去。“咔嚓”一声,碗口粗的木柱断成两截。“下一刀,就劈你的腿。”他的声音很平静,却让老板浑身发抖。
半个时辰后,工人们拿着足额的工资走出来,脸上是久违的笑容。“斧头帮”的名号,就这么在上海滩传开了。有人说他们是亡命徒,可更多的穷人知道,这是能为他们出头的好汉。
这股势头很快传到了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的耳朵里。“一群泥腿子还想翻天?”徐国梁把茶杯重重摔在桌上,他手下有七千多警察,还和青帮勾结,根本没把斧头帮放在眼里。当天下午,就有警察闯进劳工宿舍,以“聚众闹事”为由抓了三个人。
王亚樵正在码头给兄弟们分配任务,听到消息后,手里的斧头“笃”地砸在地上。“徐国梁这狗官,手上沾了多少革命党人的血,今天该还了。”他立刻叫来两个最得力的手下,“去查,这狗官每天在哪消遣。”
三天后,消息传来:徐国梁每天下午都会去温泉浴室洗澡,洗完澡正好是傍晚六点,门口的马车会等他。“就在浴室门口动手。”王亚樵铺开一张纸,画下简单的路线图,“一人开枪,一人望风,得手后从弄堂撤走,黄包车已经安排好了。”
1923年11月12日傍晚,温泉浴室门口的灯笼刚点亮。徐国梁穿着绸缎马褂走出来,正要上车,突然两声枪响划破夜空。他捂着胸口倒在地上,眼睛瞪得大大的,直到断气都没看清凶手的模样。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夜之间传遍上海滩。黄金荣在公馆里听着手下汇报,手指轻轻敲着桌面:“这个王亚樵,是个硬茬,以后少招惹。”杜月笙则端着茶杯,若有所思:“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手里的斧头,比枪还吓人。”
而此时的王亚樵,正站在黄浦江畔,把一把染了血的斧头扔进江里。斧头沉下去的瞬间,他望着远处租界的灯火,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他知道,徐国梁只是第一个,这上海滩的浑水,才刚刚被搅起来。但他没料到,这次暗杀,竟让一位军阀主动找上了门——浙江督军卢永祥的使者,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撰稿:谭福欣)
点评:
《墓碑斧影》以斧头帮主王亚樵的传奇人生为脉络,将民国江湖侠气与家国情怀熔铸一炉。作者以凌厉笔锋勾勒出码头拳脚、虹口炸舰等震撼场景,斧刃寒光中尽显草根英雄的血性与孤勇。戴笠设局、余婉君殒命等反转情节张力十足,而终章残碑松影的意象,更将侠骨丹心升华为永恒的精神丰碑。作品在历史洪流中锚定个体命运,让"杀敌无罪"的呐喊穿透时空,余韵悠长。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